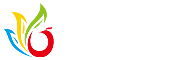音乐
希梅内斯(西班牙) 王国荣译
.
宁静的夜里。悦耳的乐曲啊,你是一汪清水。
凉爽宜人——仿佛夜来香,开在一个深不可测的
花瓶里——繁星满天际。
风逃进自己的洞穴,
恐怖回到它居住的茅舍里,
在松林的绿色丛中,
一片生机正蓬勃地升起。
星儿渐渐隐退,群山色如玫瑰,远方,果园的
水井旁
燕子在歌唱。
.
千变万化的美
丰富而变化莫测的美妙音乐,如何用语言来表达,希梅内斯运用了通感修辞来描述,首行在“宁静的夜里”,由听觉而视觉的“一汪清水”,由此而又引出“凉爽宜人”的触觉;又由嗅觉“仿佛夜来香”而至视觉——仰视苍穹,一个极为奇妙的比喻“开在一个深不可测的/花瓶里”——喻为深邃的星空,“繁星满天际”。此三行,音乐被听觉——视觉——触觉——嗅觉——复又视觉一一被奇妙的通感打通而融为一体。以下四行,音乐回到了它原初,一种天籁之音,抑或如庄子于《齐物论》中所云:“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为无作,作则万窍怒号。”,故有“恐怖回到它居住的茅舍里”之句;又如庄子云:“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各种孔穴之声也归于寂静,才有音乐“在松林的绿色丛中,/一片生机正蓬勃地升起。”最后三行,音乐之尾声,由听觉而视觉,如渐渐隐退星儿,却似“群山色如玫瑰”之艳丽,又如燕子之呢喃,余音袅袅不绝……
仅短短十行,音乐的意象繁复,万千变化,非通感不能为也。
刊于2015年1月《诗刊》
李天靖评点
《诗刊》2017年6月
.
父亲和我
吕德安
.
父亲和我
并肩走着
秋雨稍息
和前一阵雨
好像隔了多年时光
.
我们走在雨和雨的
间歇里
肩头清晰地靠在一起
却没有一句要说的话
.
我们刚从屋子里出来
所以没有一句要说的话
这是长久生活在一起
造成的
滴水的声音像折下的一条细枝条
.
像过冬的梅花
父亲的头发已全白
但近乎于一种灵魂
会使人不禁肃然起敬
.
依然是熟悉的街道
熟悉的人要举手致意
父亲和我都怀着难言的恩情
安详地走着
.
父子无言并肩的行走
这首诗是吕德安写于1984年的诗作。时隔这么多年,仍有这么多人的喜爱,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是诗人用单纯、简朴的语言,表达了他与父亲在秋雨间歇中并肩行走的经历,体会父子“都怀着难言的恩情”,颇为耐读。看诗人是如何表达的。“秋雨稍息”与“我们走在雨和雨的/间歇里”,让人感受到节律的自然安顺之美;吕德安曾在一首《诗歌写作》中写道,我“多少年,在不同的光里”写诗,在这里他写道“和前一阵雨/好像隔了多年的时光”,“好像”一词的不确定性,给了这独特情境时光的恍惚之感外,还给人以一阔大的想象空间;另外诗思的缜密可在这首诗里读到,在先写“父亲和我/并肩走着”,又写在秋雨“间歇里/肩头清晰地靠在一起”,父子深情或可见一斑的还在于因长久生活在一起,父子的相濡以沫又何需多言。又与“秋雨稍息”遥接的是“造成的/滴水的声音像折下的一条细枝条”,这是全诗中最长的长句,除了诗思绵密之外,他将雨水不时滴滴嗒嗒的听觉,用“像折下的一条细枝条”视觉的通感来表达,使感觉与形式能相得益彰。在语父亲并肩的行走时,惊见父亲已满头白发“像过冬的梅花”,才有“近乎一种灵魂”这最出彩之句,暗喻了父亲如梅花那般傲霜斗雪高洁的精神禀赋。最后意味深长的是,在这条熟悉的街道,诗人和父亲并肩安详地走着,他体会了生命中父子的邂逅,这是上苍赐予的一份恩情;在这最平常且无言并肩的行走中,让人感动的是人世间的至爱亲情。
刊于《诗刊》2017年6月
李天靖评点
.
幸福
娜夜
.
丝瓜藤上的秋天还剩下一半
我得到了
想要的
神秘的风来了
我听见裙摆上的花
对蜜蜂说:多好
与以往不同 幸福
它落到实处
落到一把青菜 一块豆腐的
精神上
被炊烟传得更远
——当它是陈旧的
这些尘埃比它新鲜
.
娜夜一首《幸福》,有别于当下人们追逐的幸福观。但她的幸福也离不开物质性,诗的前三行,就写了她在中秋“得到了/想要的”,在丝瓜藤上摘下几根丝瓜,刨了皮,炒一盘新鲜可口的瓜菜,确是实实在在的舌尖上的幸福;但她更在意心灵的另一种幸福——“听见裙摆上的花/对蜜蜂说:多好”,这种对神秘的风,“裙摆上的花”会说话的感知,对采不到蜜的“蜜蜂”而言,幸福的隐喻远不止是物质;当然,“蜜蜂”只是女诗人心灵的一个它者;诗中,女诗人对精神性幸福的有意味的掘进——“幸福/它落到实处/落到一把青菜 一块豆腐的/精神上/被炊烟传得更远”…..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意味。说到“一把青菜”,曾读过娜夜的一首《母亲》“黄昏。雨点变小”,她与母亲在雨中嘈杂的菜市场中相遇,“母亲将手中最鲜嫩的青菜/放进我的菜篮/母亲”。无须质询母爱它“还能源于什么”——但它具体而深刻,润泽心灵的是质朴的亲情,是无处不在的甘泉。于是“我”内心轻轻的一声“母亲”——不止是感动自己。如果文学有一百种“功能”,“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这是文学跟艺术最重要、最本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因此,娜夜说起一段往事,有一年,她在去河西走廊跑采访,在回兰州报社的路上,一路的雪越下越大,白茫茫的一片,对于大西北这块干旱的土地,她颇有感触地写了一首同题的《幸福》:“大雪落着 /土地幸福/相爱的人走着/道路幸福”,面对这片苍凉的世界,她说内心的感受非常丰富,她看到了:“光秃秃的树 光秃秃的/树叶飞成了蝴蝶//花朵成了果实/光秃秃地/幸福”;沿路见走着的人中,还看见了一个孕妇怀着孩子的女人,“一个孩子 我看不见他/——还在母亲的身体里/母亲的笑/多幸福”。女诗人娜夜内心孜孜不倦地追求物质与精神性双重的幸福的同时,更在意精神性的幸福追求,那是建立在平凡朴质的物质性的基础上,一种幸福的慰藉,它“被炊烟传得更远”,是一种由物质至精神力量传播的价值,“——当它是陈旧的/这些尘埃比它新鲜”,这正是女诗人娜夜所持的独特的视角,且富有哲思;她更关注的是那些卑微如尘埃般百姓的幸福,关注他们由物质而嬗变为精神性不时跃动的新鲜感受,以及生发出对万物悲悯的情怀,在她其它的诗中也屡屡所见;于看似日常性的叙述中,她能刹那间攫住意念中动人的诗意。此诗语言质朴,意象空灵且跳跃,又给人一种精神的穿透力。
2017年入选《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新一版)
李天靖评点
《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
高原牧场
萧 融
.
在高原 亦在尘埃之上
黄昏的牧场消散在静默中
鹰翅下, 经幡飘动
一道道栅栏 高过天空
仿佛在我们抵达之前
已将尘俗抑或喧嚣挡在外面
太阳下山了, 牛羊已然归栏
天上人间 , 明媚而遥远
这是世上最美丽的孤独
那个手执牧鞭的孩子, 明眸皓齿
风吹动他天堂般的笑脸
我看见他小小的内心轻轻一闪
世界小了 他长大了
.
女诗人萧融说:“我喜欢高原。高原对于我,是宗教,是图腾,是心怀敬畏。我曾经无数次走过高原,西藏、青海、甘肃、云南、以及四川的甘孜、红原藏地。在高原,有着永远的蓝天白云,阳光是明媚的,空气是通透的。特别是走在高原牧场,常常可以看到夕照下吹烟袅袅,经幡飘动,仿佛在诵读嗡嘛呢呗咪吽的六字真言。那些晚归的牛羊,自在悠闲,让人感觉空气中弥漫的牛粪味都是香的。”萧融的这首《高原牧场》,首句“在高原亦在尘埃之上””就给人一种出尘之美:写黄昏时分的静默,“消散”一词,尤为精准,细腻地刻画了高原牧场于暝色渐浓时趋于静穆的动态之美;“鹰翅下,经幡飘动”,更衬托出高原牧场的寂静,又微妙地暗示了表现出女诗人内心掀起的微澜——“幡动,在于心动”。第二节首句“一道道栅栏高过天空”,此高蹈的一笔甚为难得;是对首句的实而虚之,又为下两句张目,“将尘俗抑或喧嚣挡在外面”,一个“挡”字,表现了牧民信奉宗教的内心力量,意味深长;此时太阳下山,牛羊归栏,“天上人间,明媚而遥远”,是世上“最美丽的孤独”,此刻对高原牧场的赞美油然而生,这也是内心情感的发展;值此从写牧场的经幡、栅栏、牛羊等,由物写到人,一个明眸皓齿、天堂般的笑脸“那个手执牧鞭的孩子”,至此环境与人物的完美统一,相得益彰;“我看见他小小内心轻轻一闪/世界小了/他长大了”,于绝域高原,天地人神共处的佛界天堂,它的纯净与美丽的孤独,在落日光线踯躅的一瞬间,女诗人明心见性,那个牧羊孩子的心性,就是女诗人一颗金子般的心;她的感动,莫如说找到了内心的一种渴望——人类睽违的家园,那么遥不可及,又那么贴近。女诗人萧融说:“偶见脸有高原红的牧童,明眸皓齿,羞涩地远远看着我们,我相信此刻他们是在憧憬外面的世界。高原牧场,远离尘嚣,辽阔而寂静。在我的心里,那里的尘埃也是干净的,它们有着真正意义上的干净。在那里,我们可以卸下世俗的烦恼和忧伤,卸下平日的劳顿和琐碎,把心安放......”守护你的内心,它是一片净土;只要守护它,任何外部的力量都无法进入。
2017年入选《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新一版)
李天靖评点
李天靖《乌衣巷》
.
鸟巢
小海
.
鸟巢,从冬天
光秃的树梢上
逐一现身
却难觅鸟儿的踪影
大路上
偶尔可见
孤独的行人
春天里
树叶长出来
鸟儿们渐渐飞回
它们的巢
便再也看不到了
.
在诗人小海同题《鸟巢》散文中得知,少年的他对鸟声的敏感,曾循声于初夏麦田的深处发现过布谷的巢。“一只无比精巧的洁白得晃眼的窝就在麦丛中……椭圆的,持挂在四周略显粗壮的,但靠得紧致的麦秆上……那种细密的质地像丝绸的,或者一个放大了五六倍的蚕茧。”他还写树上的鸟巢,“鸟儿筑巢的工具就是自己身体,它们从外面用嘴衔来适用的材料交叉搭起粗陋的支撑架后,让它变得柔软、顺服,这些草梗、细枝最后服帖成精致的毛毯,不经过鸟儿用胸脯去千万次的撞击、碾压,用自己体温去熨平,获得其需要的结实的曲线,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小诗《鸟巢》写于九十年代,他回忆说,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租住于城郊,道路两旁有不少高大的树木。上班路上不时会听到各种鸟儿的鸣叫,感触很深。树木为人类蔽荫,也护佑着鸟儿们。一年四季,树叶的生长到飘零,直至落尽,鸟儿们和它们的巢最有感触。另一方面,在自然界中存在的鸟巢或也像人们那样通灵,寻它千百度,却在不经意中自性显露,又在自然的节律中隐藏不见。《鸟巢》写的树上的鸟巢,于乡间乃是平常之物,却由他的生花妙笔,展现出魔术般的魅力。他先写了冬季在光秃秃树上鸟巢的逐一现身,“却难觅鸟儿的踪影”,孤独的行人,只是作为衬托;这里让人去想象的是树叶渐渐落光了;与之相对的是春天,树叶长出来了,“鸟儿渐渐飞回”,而后来鸟巢便再也看不到了——鸟巢被渐渐长出的树叶遮蔽了。 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的精神写不出,以草木写之。”此诗于以树叶随冬春两季的变化,鸟巢或现身,或被遮蔽,鸟儿随季节的变化,亦忙不迭的飞走又飞回,运用了有些令人晕眩的对比修辞,在它看得见或看不见时,却自足而孤独的存在;鸟巢作为自然的造物,它永远是侯鸟们永远的居所,于永恒时间中的显隐,仿佛是一种神性的存在。此诗的语言背后,诗人不动声色地以两个不同季节的关于鸟巢与周边环境的情景对比说话,与鸟形成对自然、世界的认知与情绪反映的对比。在对待自然上,人其实远远不及鸟的那么“顺其自然”。
2017年入选《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新一版)
李天靖评点
《新诗鉴赏辞典》撰稿人
.
母亲的灯
刘向东
.
那灯
是在怎样深远的风中
微微的光芒
豆儿一样
.
除了我谁能望见那灯
我见它端坐于母亲的手掌
一盘大炕,几张小脸儿
任目光和灯光反复端详
.
啊富裕的夜晚
寰宇只剩了这油灯一盏
于是吹灯也成为乐趣
而吹灯的乐趣必须分享
.
好孩子,别抢
吹了,妈再点上
点上,吹了
吹了,点上
.
当我写下这些诗行
我看见母亲粗糙的手
小心地护着她的灯苗儿
像是怕有谁再吹一口
她要为她写诗的儿子照亮儿
.
哦,母亲的灯
豆儿一样
在我模糊的泪眼中蔓延生长
此刻茫茫大野全是豆儿了
金黄金黄
.
那金黄金黄的
涌动的乳汁啊
我今生今世用不完的口粮
.
《母亲的灯》这首诗是诗人刘向东写在1993年秋天诗刊社第11届青春诗会上。他说,一个停电的夜晚,眼前忽然亮起母亲的灯。之所以如此,是有着深在的根源的。诗人出生于燕山深处的一个农家,自幼做过农家孩子该做的一切,经受过艰辛岁月的磨砺,深知大地的贫瘠和生活的重负。乡村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那历经沧桑的屋舍和一代代流逝的人群,比梦幻更虚渺,比生命更真切,形成了他活动的背景,使他无法不面对和切人此在的一切。这种切入是对深度时空的一种探询和追忆,作为在场者,他力求让复述与显现交融,让人分不清远近和彼此。他借助母亲的灯,从现实这惟一的入口历经过去和未来。至于其中的细节,看似经过提炼,其实是现成的,本来就是那样,“点上,吹了,吹了,点上……”
以“母亲的灯”为题的此诗,颇具非凡的艺术魅力。其主体意象如题所云,即“母亲的灯”。“那灯/是在怎样深远的风中”,首二句一下子将这盏灯推至极远,如电影远至又远的远镜头;“深远”之前又以“怎样”这一疑问代词用作修饰此“一灯如豆”在“风中”颤动,微弱且小,但历历在目,再大的风也无法吹灭。
第二节写“我”洞若观火,灯竟“端坐于母亲的手掌”,乃直觉或心见,于点题之外,一句“任目光和灯光反复端详”传神写照,“灯光”或拟人化为母亲的隐喻,与炕上的几个孩子的目光融和在一起了——之后,“啊富裕的夜晚/环宇只剩下这油灯一盏”,颇为反讽,在那物质贫瘠的时代,农村孩子的游戏只有一盏油灯,“几张小脸”与母亲一起分享起“吹灯”的乐趣,点上,吹了,吹了,点上,不亦乐乎;行文至此笔锋一转,母亲为“我”写诗“护灯”,小心护着她的“灯苗儿”,再为“母亲的灯”点题——紧接一句“哦,母亲的灯/豆儿一样”,诗思绵密,照应首节“微微的光芒/豆儿一样”,由此直至情感的峰巅,“我”被母亲的爱深深感动,“豆儿一样”(光芒),“在我模糊的泪眼中蔓延生长”,抑或为母爱的光芒:“此刻茫茫大野全是豆儿了/金黄金黄”,梦境一般似的,乃为造境。
最后一节三句,意象的嬗变“金黄金黄”豆儿的光芒成了“涌动的乳汁”(暗喻“母爱”之深广),成了“我今生今世用不完的口粮”——其意象均由“一灯如豆”而来,反而观之,其变化由微小且深远,渐近“端坐于母亲的手掌”,最后若“此刻茫茫大野全是豆儿了/金黄金黄”,从“那灯”如豆的语言内部始,最后为“母亲的灯”的光芒深远浩大,乃是照彻“我”诗心永不枯竭的光明,亦如诗人刘向东所说:“我的几乎所有诗,其实都是献给母亲的,母亲就是大地,就是爱。”
诗人牛汉也曾为他的《母亲的灯》(诗集)写序,序中说:“母亲的灯,这四个字真神真美!熠熠生光!一下子照亮并显示出一种神圣的美丽的境界。我对这首诗的境界和所有的细节都异常熟悉,来到人世上第一眼看见的光,不是来自太阳,是一盏摇曳着红亮光芒的油灯,还有油灯一般的母亲的眼神。人生长长的画卷和诗篇在母亲的灯光下打开了。”
《母亲的灯》是一首情感浓郁的诗,意为表现母亲对诗人诗歌创作爱的呵护与再造之恩,其诗的起承转合,以豆灯为喻,意象奇特嬗变不测,貌似乡土,内里颇具特朗斯特罗姆超现实主义风格。
2017年入选《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新一版)
李天靖评点
(荐稿:朦胧诗社社长 牧野)
标签:#高原红歌词意义